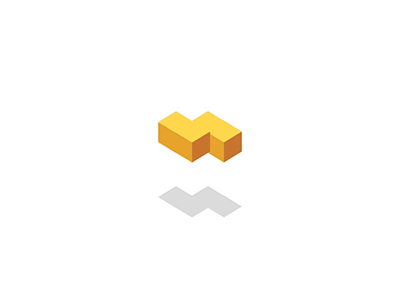月落乌啼霜满天,
讲枫渔火对愁眠.
姑苏城外寒山寺,
夜半钟声到客船.
空城,是我。
经年行路,风霜中最惦念的是故乡那扇小轩窗,几次梦里潜入芭蕉院,‘看见少年的她梳出自发。她的夜半孤影总让我不能放心.
无家,可以禀明死生;无兄弟,可以话桑麻;等我的人,我却无梦相赠。
身, 已如秋蓬,心,寄托行云流永,我怎能再做春闺梦里人? , 。
故里重回,旧友流散;与我缔结初梦的人也已儿女成行。最后一个牵动心绪的人既已建筑家室,守住了春花秋月,我可以完全放下了。
她不会知道那个出远门的人,枯坐在市集一隅,远远看她提篮牵儿从眼前走过。
她不会听到,当她与小贩评论斤两时,我幽微的唱叹。
她不会知道,多少次我在梦中重回江亭,折了春柳,放在她打水浇衣的井边。
她不明白,我仍然熟诵当年的誓词。每当与锣鼓花轿错
身时,那誓言又绞痛了我的心。
她怎能了解,我山高水长地想遗忘她的容貌,又在异乡庄园寻找似她身影的人。
我仍是一个不告而别的人,毁了她少年春闺的人,辜负她的人。
当她走入另一个屋檐,她的少年空城也归还给我了。
那么,除了遥遥一见,我焉能怀抱两座空城走到她的面前,把残枝败柳的故事又说一遍呢?
让她永远不知道我是生是死,则她可以安然无恙地被守护着;让她永远怨一个名字,则她可以平安地过眼前日子,不会回头找空城。
离开故里的那夜,我是空了的人。
秋霜已经爬满天,江边停泊的旅舟,或踏歌饮酒,或沉沉地眠睡。三两声夜鸟,更添秋夜静寂,水波摇晃舟身,亦摇晃榻上的我仿佛我与江水、秋霜都是亘古的醒者,靠了岸,又离了岸的。如果,子夜想歌,有什么比叹息更畅怀?
子夜想醉,有什么比忘川之水更能断愁?
忽有钟声隔江传来、染了秋霜的声音听来分外清寂,仿佛偷听了我的心事后,似有似无地为我说经.
说:空山已被雾境收留了:空城,不妨赠给客船去货运;松树林寺里有一口闲钟,正等着天外客,陪它说梵音.
美丽的茧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,让我保有我的茧。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,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,以回忆为睡榻,以悲哀为覆被,这是我唯一的美丽。曾经,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赤热的心肠。怎么回事呀?它们开得多美!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,教给我再生的秘密。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,我听到杜鹃颤微微的倾诉。每一度春天之后,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。
如今,仿佛春已缺席。突然想起,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,三月春风似剪刀啊!
有时,把自己交给街道,交给电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,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,随便坐着,有人来赶,换了一张椅子,又有人来要,最后,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,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,这才是自己的。被注定了的,永远便是注定。突然了悟,一切要强都是徒然,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,一出生,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,不管愿不愿意。乖乖随着安排,回到那个空间,告别缤纷的世界,告别我所深爱的,回到那个一度逃脱,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。当铁栅的声音落下,我晓得,我再也出不去。
我含笑地躺下,摊着偷回来的记忆,一一检点。也许,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,也许,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,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,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。很认真,也很死心塌地,一衣一衫,都还有笑声,还有芳馨。我是要仔细收藏的,毕竟得来不易。在最贴心的衣袋里,有我最珍惜的名字,我仍要每天唤几次,感觉那一丝温暖。它们全曾真心真意待着我。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,怀抱着它们入睡,已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。
够了,我含笑地躺下,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。
每天,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,拉我离开心狱,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,一切重新再来。她们比我珍惜我,她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结我的手铐脚镣,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。我甘愿自裁,也甘愿遗失。对一个疲惫的人,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,对一个薄弱的生命,又怎能命它去铸坚强的字句?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,那么就由它的性子吧!这是慷慨。
强迫一只蛹去破茧,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,是否就是仁慈?
所有的鸟儿都以为,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。
有时,很傻地暗示自己,去走同样的路,买一模一样的花,听熟悉的声音,遥望那窗,想像小小的灯还亮着,一衣一衫装扮自己,以为这样,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,至少至少,闭上眼,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。
如果,有醒不了的梦,我一定去做,
如果,有走不完的路,我一定去走;
如果,有变不了的爱,我一定去求。
如果,如果什么都没有,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!这二十年的美好,都是善意的谎言,我带着最美丽的那部分,一起化作春泥。
可是,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。时间像一个无聊的守狱者,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。空间像一座大石磨,慢慢地磨,非得把人身上的血脂榨压竭尽,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,才肯利落地扔掉。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,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。生活是一个刽子手,刀刃上没有明天。
面对临暮的黄昏,想着过去。一张张可爱的脸孔,一朵朵笑声……一分一秒年华……一些黎明,一些黑夜……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,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。被深爱过,也深爱过,认真地哭过,也认真地求生,认真地在爱。如今呢?……人世一遭,不是要来学认真地恨,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。在我活着的第二十个年头,我领受了这份赠礼,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,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。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,我能怎样?认真地流泪,然后呢?然后怎样?回到黑暗的空间,然后又怎样?认真地满足。
当铁栅的声音落下,我知道,我再也无法出去。
趁生命最后的余光,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。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,把熟悉的面孔,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,把生活的扉页,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,也一并装入,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。把自己也最后装入,苦心在二十岁,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。把微笑还给昨天,把孤单还给自己。
让懂的人懂,
让不懂的人不懂;
让世界是世界,
我甘心是我的茧。
浮舟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,那是秋天的手指。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,夜将它吹凉。
宁谧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,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,在打盹的小舟上。然而,岁月是个撕书人,把故事章节塞入每一扇窗户,开几朵微笑的,流几滴泪的,浮世如倒影。所以,飘着风信子与熏衣草的春日,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,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;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暮日上空响亮;总有迷路的鸽子,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。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,你要听新故事吗?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,笑着说:总有回家的人,总有离岸的船。
空篮子她老是梦到丢东西。
确实地说,不是现实生活中拥有的东西在梦里遗失,是当夜梦里刚拥有的却立即在意外情节中丢了。
“见鬼!”她一面煮早餐咖啡一面嘀咕,甚至突然跑进盥洗室对镜中的自己说:“你干脆把我丢掉算了,我会感激你。”口气像对情人抱怨。
又来了,昨晚。梦见自己提一只很大的藤编篮子,藤的色泽非常雪亮。装的全是发光的宝石别针,有一支长得很象勋章菊,其他的因参差交叠无法辨识形貌。看来都是她的收藏,满满一篮。她似乎在赶路,赶火车或轮船,仿佛要到遥远地方。她着急地提着篮子从人群中逆向穿过,由于只有她往反方向走,篮里的别针被某名陌生女人碰掉了几个。她弯腰捡,赫然发现路上铺满各式各样的别针,不知谁的。她精确地捡起自己的,虽然混杂其中,亦能辨认自己的别针异于其他。正要走,忽然蹿出一名女人拦着她,责备她侵占。此时,刚才碰她篮子的陌生女人亦堵过来,邪邪地笑着。她同时明白两件事:铺在路上的别针是那名女人的,而邪笑的女人碰她的篮子是一桩阴谋。她看了看脚下大大小小的别针,都是粗糙玩意儿。她向她解释:“我的别针跟你的不一样。”她们二人反问:“如何证明那是你的?”
她在梦中被问倒,怎么去证明原本不需证明的?她明知道两名女人恶意刁难,可是,虽然无法以强有力的证据道破它们的恶意,而对方可以严辞相逼,诘问她的清白。梦中,她高高举起提蓝,像泼水一样,别针悉数掉到地上。她诡异地笑着:“那!都是你的了!”
她提着空篮子,消失在梦中。
推荐阅读:
梁实秋散文集
贾平凹散文精选
余秋雨散文集
徐志摩经典散文集
席慕容散文精选